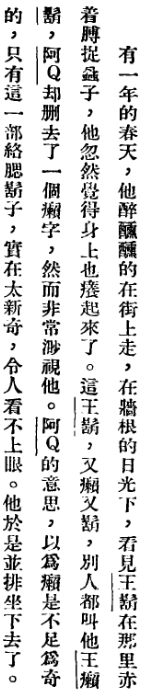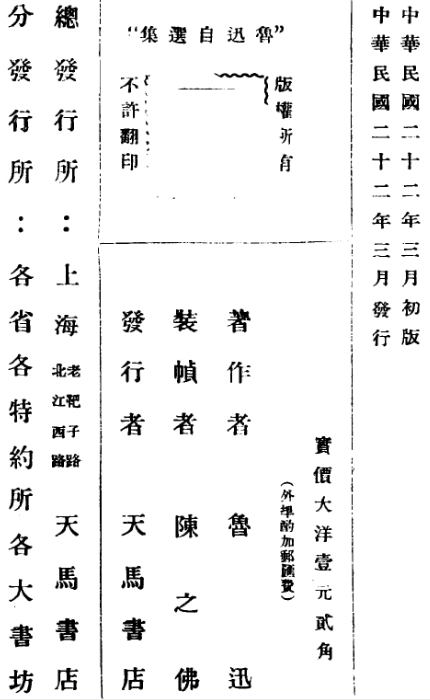漢字的道理
原發於: http://www.pkucn.com/viewthread.php?tid=245669
理和習俗、習慣不是一回事。本來孟子有一段很好的話闡明甚麼是理,但是考慮到把它展開了講實在囉嗦……以我的管見呢,所謂理就是「人同此心」的東西。
比如有些人(也沒準兒是大多數人)打噴嚏的時侯從來不以手掩口鼻,這不等於說有此習慣的人就認為這樣做有理。形成這樣的習慣往往可能是出於對身邊的一些所謂小事不留意。趕到不得不留意時,好比在SARS期間,他恰好得了感冒,自己的孩子正在身邊跑跳嬉戲,這時來了一個噴嚏,他不自禁地就會把手掩上了。
漢字裏就藴藏著這樣的道理,你不留心就看不見。好比有一次我在墓園裏信步閑遊(當然是掃完墓 )一邊走馬觀花地讀墓誌銘消遣,發現有一桶碑後刻有成語曰:含辛如苦。顯然,這個詞立碑者是用錯了,我就很替他惋惜。立碑者對墓主(其妣)的哀思不難理解,其拳拳之心也沒有甚麼可懷疑的。僅因一字用錯,其情感表達的真切度就打了折扣。雖說讀者多能諒解,但是總存著一點遺憾。不是我刻意咬文嚼字,而是通過這個錯字能看出屬文者沒有眞正理解這個詞。將不能理解的詞用在文章裏,一旦拆穿,又怎麼能不對讀者造成生硬的感覺?
茹字原義爲「根相牽引貌」,後以「食菜曰茹」。聯繫「茹毛」「茹素」,很容易就能想像出「茹苦」時吞食野菜那種草萊縱橫的情景。一個草頭,正是理解這一串詞語的關鍵。「含辛『如』苦」之病僅限於生硬,更有因不認識茹字而將含辛茹苦訛寫成「寒心如苦」的,這樣意思就全變了,由艱辛而寒心,不僅博不得讀者的諒解反而要招來嘲笑。
爲甚麼偏偏揀一個沒有被「簡化」的字來說事?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讓那些對漢字的理視若無睹的人,即使不怎麼認得被「簡化」了的「繁體」字也都能明白這個道理:想說好、用好、理解好漢語,漢字纔是不二法門!你對漢字中的學問不感興趣,那是你的自由,可若是因為漢字能力差而導致你漢語也說不好,則是你的損失。
再舉幾個例子:
謎字原來不念迷,而念作去聲--在敝鄉談中只有兒化音,將猜謎稱作「破謎兒」。迷字<說文>曰:惑也。<易·坤卦>中有「先迷後得。」結合「言」旁,聯繫所行者爲行(去)、所譽者爲譽(去)、所聞者爲聞(去)之類,就能明白謎是迷的派生:所以惑人之言語也。
如前所舉,好好、爲為、難難、惡惡等「如字」和破讀的對立,恰恰是現行漢字中粗糙的應該改進的地方。又如占的平去、舍的上去,兩讀的關聯極不容易看出來,或者壓根就是不相干的,只有添上佔和捨的字形,纔能確保漢語學習者對這兩組含義得以清晰識別和準確領悟。想得到清晰準確的漢語,必須用清晰準確的漢字來表記--這個道理很迂奥難懂嗎?
舉個書裏邊的例子:記得我在簡化字版的<吶喊·阿Q正傳>中讀到:「这王胡,又癞又胡,别人都叫他王癞胡」--當時,那一瞬間就很迷惑,這個胡究竟是胡來的胡,燒煳了的煳,還是鬍須的鬍(因為按敝鄉談的習慣,只有煳字勉強可以用作形容詞)。想不出個如之何來,只好硬著頭皮往下讀:「……癞是不足为奇的,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,实在太新奇……」這纔恍然。仿佛是說相聲的鋪平墊穩,逗得你心癢難搔時纔抖包袱?你說,一種現代文字含糊到猜謎似的程度,好不好笑?
我這裏不打算舉形聲字貫通古今超越南北的例子,因為對講官話的人--中國的大多數--這個話題顯得枯燥無味。一者,對古詩詞真感興趣的人實在是不多。而且,即便是在這不多的詩詞愛好者中又有一半是恨不得要革格律的命的。再者,你講别的方言,這裏合那裏合的,有小心眼兒的官話人聽起來就好像是在奚落他,他心裏抵觸,我說了反而適得其反。那麼,不如大夥都把聲符當成抽象的符號來看。比如,你認為坝是水坝,那麼平坝怎麼講?你認為仆是奴僕,那麼前仆後繼怎麼講?如果你認為钟是大個的鈴,那麼不泛千钟应不醉怎麼講?如果你認為获是捕獲的意思,那麼收获怎麼講?如果你認為坛就是個土臺,那麼醬菜坛子怎麼講?如果你認為葯是治病的東西,那麼花葯怎麼講?……
漢字最大最硬的道理就在於漢語離不了它。如果你讀到此處也有這樣的感想,那麼我很欣慰,意味着咱們就都算沒白費這工夫。否則……never mind ;)